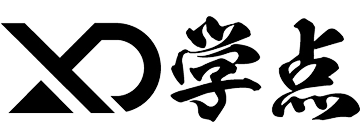切换为使用验证码登录
曾几何时,Science子刊也曾是学术圈的“顶流认证”,是万千科研工作者的梦之情刊。
但近年来,关于其沦为“洗钱水刊”的争议甚嚣尘上,接二连三的学术不端丑闻更是让其名誉一落千丈。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顶级期刊的光环遭遇商业模式的侵蚀,科研公信力与资本利益的博弈时,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今天,就让赛恩斯小编和您一起探究Science子刊的“隐秘角落”。
“顶流”的坠落:
学术权威如何被商业逻辑反噬?
《Science》子刊的商业化困境
Science出版社的盈利模式依赖于两大引擎:高额订阅费与开放获取(OA) 版面费。
作为全球顶级期刊的《Science》,自1880年创立以来,以“推动科学进步”为宗旨,但其出版商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近年面临严峻盈利压力。
因此,为扩大收益,AAAS接连推出数十个子刊(如《Science Advances》《Science Immunology》),通过“开放获取(OA)模式向作者收取高额版面费正刊《 Nature》 和 《Science 》用来吸引优质稿源,而未能发表的文章则转投到这些子刊上,通过高额的版面费盈利。
以《Science Advances》为例,单篇OA费用高达4,500美元,而该刊年发文量超2,000篇,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近千万美元!

图:AI统计部分Science子刊版面费情况
但这样的盈利模式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激增的发文量和低质量文章的涌入,接踵而来的,就是旗下期刊频频爆出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丑闻,逐步侵蚀了创刊人员经年努力构建起来的公信力。
“流水线评审”与学术腐败
近几年,Science部分子刊为了追求发稿量,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审稿标准,让“论文工厂”趁机渗透子刊、.滋生“特刊”灰色产业链,严重助长了学术不端的风气,引发了一系列的撤稿丑闻。
据Retraction Watch统计,2020-2023年,《Science》旗下子刊撤稿量激增30%,远超传统顶刊。具体案例不胜枚举:
2021年,《Science Signaling》因接收多篇中国论文工厂生产的文章引发争议。这些论文数据重复、结论牵强,却通过第三方外包的“快速审稿”服务被接收。调查发现,作者多为医疗机构人员,发表动机直指职称评定与经费申请。
2023年,《Science Signaling》撤回印度某团队7篇论文,揭露第三方“论文工厂”通过贿赂编辑批量发表论文的灰色产业链。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STOTEN,隶属Elsevier但模式相似)曾因“特刊(Special Issue) 泛滥”被列入中科院预警名单。出版商通过邀请非专业客座编辑组稿,接收大量低质论文并收取高额费用。类似操作在部分Science子刊中亦有迹可循。
《Science Advances》2022年撤回一篇量子计算论文,因核心数据涉嫌捏造。
.......
“洗钱”背后的利益链:
谁在助推水刊泛滥?
Science子刊(如Science Advances)近年来被质疑为为了赚钱而降低学术标准,发表大量低质量文章的“洗钱水刊”,其中,必然离不开出版社、作者和机构的共谋的推波助澜。
出版商:利润驱动的“双重标准”
1. 主刊与子刊的“分池策略”Science主刊因刊用率极低(约6%),大量被拒稿件被推荐转投子刊SA,且部分转投流程可能简化同行评议。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策略,使得子刊成为主刊的“泄洪口”,导致稿件质量参差不齐。例如,NC和SA均被指出包含大量主刊拒稿后“降级发表”的论文。
2. 开放获取的高昂费用与审稿宽松SA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为4950美元,远低于NC的6790美元,但仍属高额收费。部分学者认为,出版社为维持收入规模,可能对稿件质量把控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主刊维持学术声誉,另一方面通过子刊扩大发文量以吸金。例如,2023年SA发文量超过2000篇,而NC更是高达7910篇,庞大的体量可能削弱审稿严谨性。
3. 对特定国家或机构的“宽容”数据显示,中国学者在SA和NC的发文占比均达12%,部分研究机构为追求国际发表指标,可能倾向于选择“高影响因子但审稿效率快”的子刊。出版社对此类高投稿量的国家可能存在隐性偏好,甚至默许低质量稿件通过以维持市场份额。
尤其是国内高校“唯SCI”评价体系下,许多学者为快速晋升,选择付费发稿。某985高校教授就坦言:“子刊影响因子高,审稿比主刊松,即便交钱也划算。”
学术功利主义:作者与机构的共谋
1. 论文工厂与学术不端产业链
论文工厂通过伪造数据、同行评议甚至贿赂编辑的方式批量生产论文,其目标常锁定开放获取子刊。例如,中国某论文工厂“橄榄学术”被曝向期刊编辑行贿以加速发表。此类行为直接利用子刊审稿流程的漏洞,将学术出版异化为“付费即发”的交易。
2. 机构对署名权的滥用部分机构为提升学术产出,默许“搭便车”署名行为。例如,某投稿因共同第一作者贡献不均、跨机构合作真实性存疑被直接拒稿。此类操作模糊了作者的实际贡献,间接导致低质量论文通过“包装”进入子刊。
3. 科研经费的畸形分配中国学者每年向开放获取期刊支付的费用保守估计超7.6亿人民币,其中大量资金来自科研经费报销。这种“经费驱动发表”的模式,使得学者更倾向于选择高接受率的子刊,而非严格筛选的传统期刊,进一步加剧质量滑坡。
双重标准与共谋的交互作用
出版社与作者/机构的利益链形成闭环:
出版社通过子刊扩大盈利,同时依赖主刊维护品牌;
作者/机构利用子刊的高效审稿与相对宽松标准,快速完成考核指标;
论文工厂则填补了双方对“数量需求”的灰色地带,形成产业化造假58。
这种交互作用,毋庸置疑地导致了子刊的学术公信力一步一步地受损。
破局之法:
出版商、作者与制度的三重责任
如果还有出版商仍然保有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而不想沦给彻头彻尾的“洗钱”商人(虽然从目前的出版管制下,单纯只想圈钱的出版模式根本不可能长久发展),完全可以不断摸索制度和政策,剥离商业与学术决策,找到“赚钱”和“科学传播”的平衡点。
对于出版商而言,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旗下子刊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如设立独立编委会监督子刊质量,严格把控子刊质量;严格区分子刊与主刊的审稿标准,避免“降级发表”成为默认流程、公开审稿流程与撤稿数据,接受学界监督;同时,限制子刊数量和发文量,建立客座编辑追责机制;以及合理定价OA费用,避免学术资源垄断。
作为学者,我们同样需要为健康的出版生态贡献力量。我们需要逐步拒绝“短平快”发稿诱惑,优先投稿行业认可的专业期刊,核查期刊口碑与历史,专注研究本身价值。同时支持并参与“预印本+开放评审”等新型模式,减少对商业期刊依赖,推动生态多元化。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也要肩负起建立多元科研评价体系的责任,从而弱化影响因子权重,例如资助高质量开放获取平台,打破出版巨头垄断等等,加强跨国合作打击论文工厂,如UNITED2ACT联盟的成立,同时规范开放获取收费机制等等。
编者按
Science子刊的困境折射出学术出版过度商业化的系统性风险。而学术出版的商业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它让知识传播更高效,却也使科学精神在资本游戏中步履维艰,当科学探索沦为资本游戏,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期刊的声誉,更是全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唯有回归“求真”本质,才能避免《Science》子刊的悲剧在其他领域重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你是否曾为发表论文选择“水刊”?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察与思考。